「超日常」:場所的習題
文/盧思諭
以小說敘事為起點,現實的北區藝術聚落陷入了虛構的維度,成為創作者非得翻牆而出的想像框架。這是一種逼近的手段,參展的藝術家必須面對它、橫越它,或者試圖擺脫它。場所原本的故事,早已隨著校方改建工程逐漸流失,原來的氣味如流沙塌陷,正如駱以軍在《翻牆者》裡描述的的垂敗廢墟。現實世界裡填滿的餡料早已翻落,唯獨剩小說裡的各路人馬,汲汲營營地在故事架構裡奔走。牆隙的光成為抒情的敘事,雜蕪的空屋轉瞬為古典遺跡,同等於小說中的遙遠殖民星球、群礁般錯長出的人生——創作者們如何任想像力蔓生於其間?針對場所而生的感性經驗,如何從創作這端踏入作品?答覆似乎就在唾手可及之處,透過藝術的實踐,藝術家如此回應這道創作的習題。
可感性極高的賴志盛《浮洲》作品,眼光直接越過了小說,落到這個場所本身。它屬於展間內裡的素描風景,從管線孔洞延伸出來的鋼索,給出了與小說截然不同的意象張力,如同將敘事的權利歸還給房子——儘管房子什麼話都沒說出口,僅剩沿線傳送而來的震動和顫抖。這幅因人為踩踏而隨之晃動的《浮洲》,如橫跨的口子,讓現實裂開,筆直的邊緣切出虛與實,實際上也是觀者腳下迎來最直接的感受。一個略微懸離地面的空中浮板,在意象上代表著所有創作者欲開闢出來的另一世界。意象被允許登入,開放的同時,也以時而僵硬緊繃的線路聯繫著現實的展場空間。意象透過真正的高牆磚瓦造作出的結構予以成立,成為被真實世界包裹的一份子。那麼對比於小說創作呢?經由現實的摻雜攪和與浸透的文字,更襯托出《浮洲》在裝置藝術類型上的明朗層次。

皮埃爾-勞倫特・卡希爾在D區展間的《片刻》與《錯置》,從文本中汲取了一個房間意象,創造出令觀者不安的時光之屋,和史蒂芬・帝德的《無暗之界》氣質是若干相通的,因為他們都發現了光之於暗室中的巧妙。人造的也好、窗外折進來的也罷,光線讓作品的主軸變得通透漂亮。儘管它們有極大的可能性,可以被轉譯成語言上各種暗喻象徵,或抒情啟發,但是如果不以言詞試圖翻譯,或許更能保留無法言說的曖昧性,並將隨著展覽的結束,成為觀者不斷回望凝視的「那個」記憶——或許閱讀小說也是這樣的?意象將隱隱佔據觀者的內在一隅。

讓我們想像一個畫面:以有章藝術博物館內透著白色光暈的閱讀膠囊為軸心,星佈在北區藝術聚落的數個展間環繞著它。蔡宛璇《植與蕪》與周曼農《高熱103°》,以文字的形體和語言的聲音,回應著小說這個隱形文本。在此,藝術家不願受到小說本身的故事內容牽制;蔡宛璇以文字印刷術的角度,巧妙地迴避出一條路,並展開屬於當地水文脈絡的探討,延展成如圖像詩般的視覺印象。周曼農讀劇的聲音,在希薇雅・普拉斯的假想舞台上,注入了言語的韻律。文字這條諾大的洪流,從各處的基底層滲透出來;《翻牆者》如同一則秘密象徵,一股來自中央的無形引力,又如蚌類生物亟欲征服的嵌入硬質物,吸附從各方前來、珍貴的創作。
於此同時,劉和讓在《大觀別墅-極短篇》裡,沈浸於自己之所以成為青年藝術家的憶想中。拋給周邊鄰居住戶的信件,擲地無聲,書寫的動作安靜地落在複寫紙上,一遍又一遍地以文字爬梳著思緒。輕輕覆在這個展場的過去、今日和將來,形成藝術家內在時序的對話,對照著小說家筆下被濃稠的虛構筆法所確認的世界,場所化成被輕煙迷霧籠罩、不被定義與定型的真實所在,卻勾懸著藝術家仍持續進行的等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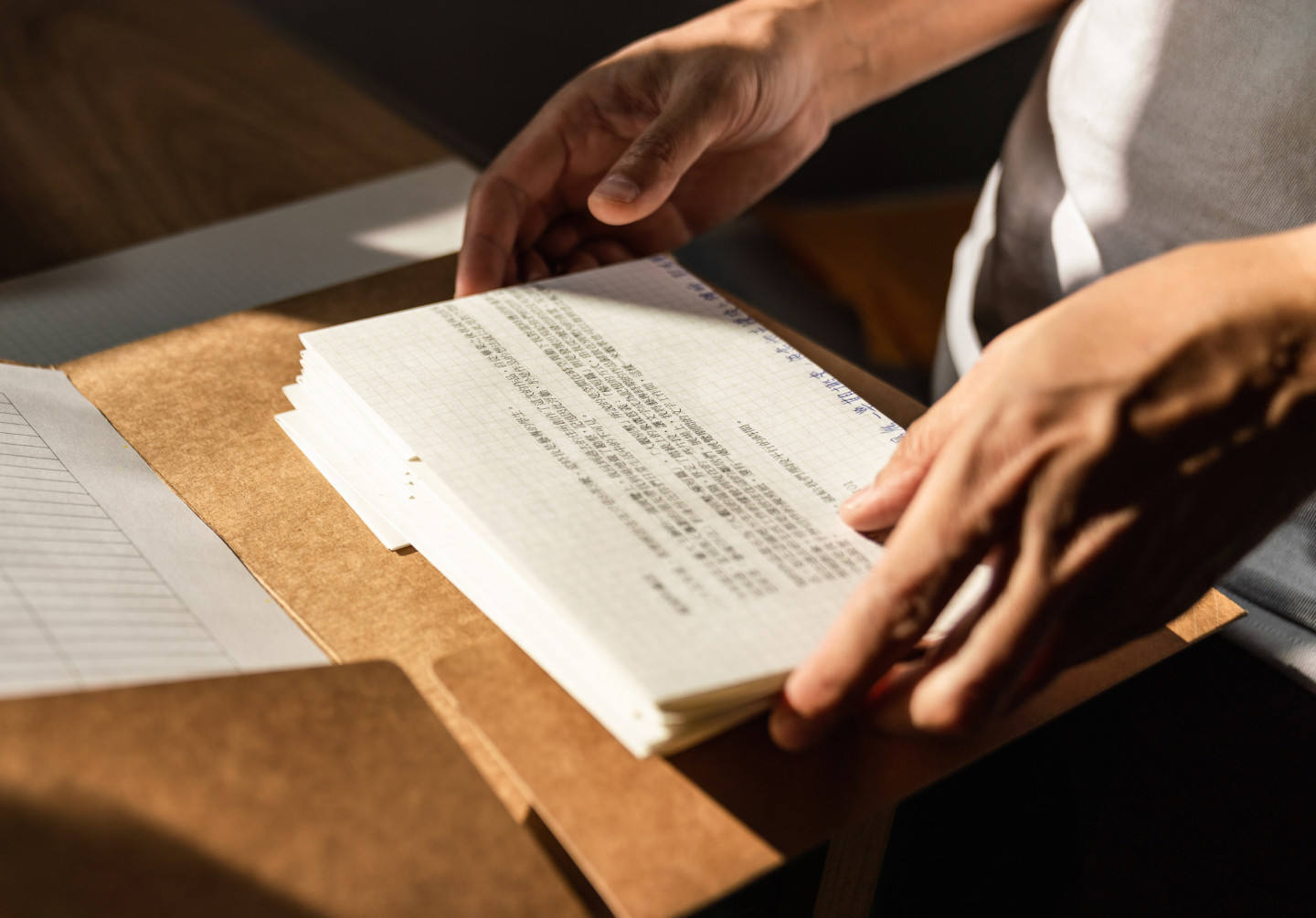
傑夫・帝森《後窗》則在視覺上以日夜全景的循環影像,與小說中對屋中之人的窺看彼此共鳴,亦與有章藝博館內的伯恩德・歐普《場景調度》作品遙相呼應。以電影為腳本的再創造,猶如在虛構層次上的拆解和攪動,敘事角度上的根本變動,拉出了《後窗》裡的後設性,觀者面對的是自己將如何觀看這則虛構的故事。在此之後,更多的問題開始夾纏不清:當我們意識到北區藝術聚落的這些場所,已經被各種述說方式重疊交錯,不再是單純的所見即所得的現實,它漸次開展出了對自身的觀看和展示,也包含對「日常」此一主題的凝視。

作為文本的有形呈現,有章藝術博物館裡的駱以軍X張君懿「閱讀膠囊」,獨立圈出一個角落,觀者忘卻它也好、識得它也罷,無論是何者皆不影響「超日常 Daily+」觀展的樂趣——「日常」主題是露於外的第一層可見位置,但銜餌而上、察覺展覽機制下的文本運作,進而能觸及各件創作深植的土壤層。文本的存在和對藝術家進入的設定,使展覽變成一場機遇的遊戲,藝術家們身在其中,對於最終所展呈的成品,不再能噤聲不語。以這樣虛構的小說作為首件發起作品,對應北區藝術聚落其來有自的人文脈絡,是相當聰穎的手法,同時也將一場發生在此地的展覽,回歸至「創造」所屬的範疇。而這道場所的習題,不只是給予參展藝術家,也是策展人強烈意識設下的題,考驗如何將這些作品安置於展示場所中,和文本產生若即若離的關係。
